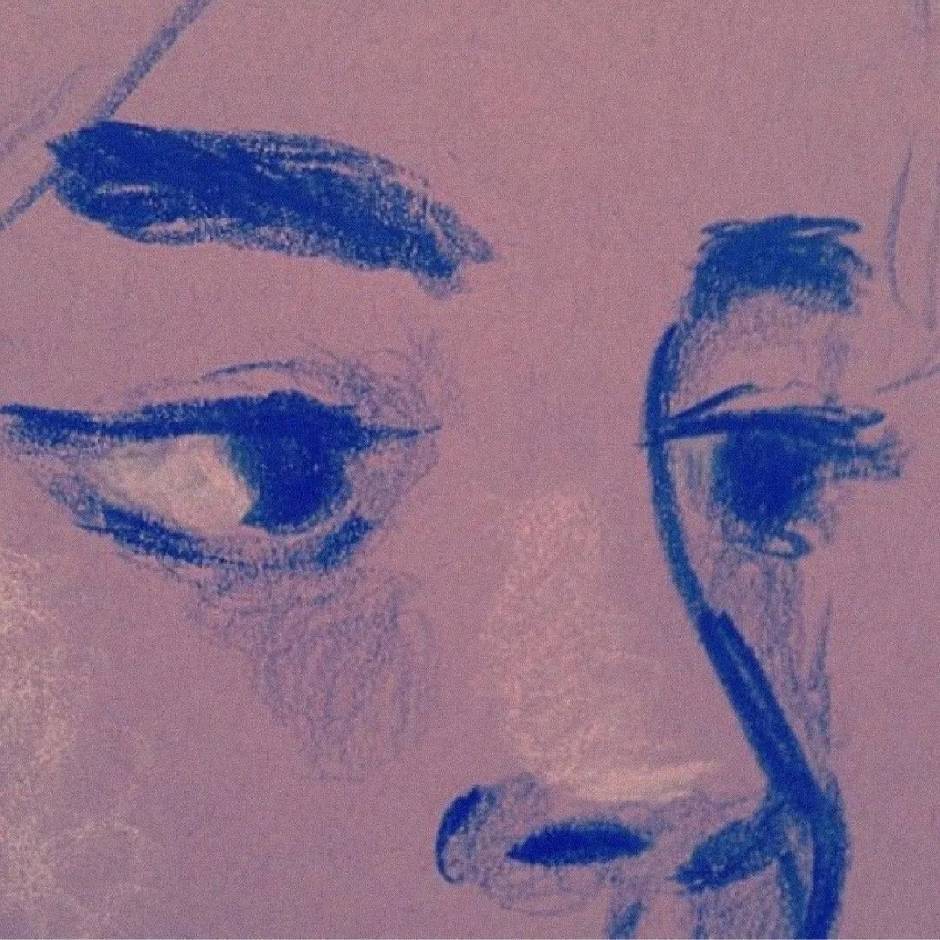当缓冲地带用完时
编辑1. 学术新衣
奇怪的是,那些曾经让我失眠的焦虑,现在看起来都变得轻飘飘的——原来时间真的会稀释所有烦恼,或者说,我比想象中更擅长糊弄事情。
我的毕业论文拿到了优秀答辩资格,这个结果让我在宿舍笑出声来。
毕竟这篇东西的诞生过程堪称当代学术行为艺术:我像个流水线监工,对着GPT反复输出"这段不行重写"、"整合这几篇论文的数据"、"降低重复率"之类的指令。
最讽刺的是,GPT像个被过度调教的学生,回答越来越稳定,反而失去了最初那种灵光一现的惊艳。有时候我盯着屏幕,恍惚间觉得我们俩的角色完全颠倒了——它才是那个需要导师签字确认的毕业生。
最后我放弃了优秀论文答辩——与其说是对学术的敬畏,不如说是对二次答辩压力的投降。
参加毕业典礼那一天,许老师告诉我:"嘿嘿班主任特意研究了你的论文内容,就等着二辩审你呢,还在办公室说'也就那样吧'。"
我们相视嘿嘿一笑,心照不宣地完成了这场学术cosplay的谢幕演出。
2. 消失的成年人身份
离校后的第十天,我的行李箱还摊在房间角落。衣服堆成的小山慢慢塌陷,就像我对"独立生活"的想象一样,在现实里逐渐变形。
理论上,23岁应该是个标准的成年人了。但我在家里有种奇妙的时空法则:我的游戏时间被自动压缩到父母睡觉后的深夜,而所有关上的房门都会在一个小时内被各种理由敲开。
最神奇的是,我发现自己正在退化。大学时能同时搞定任何事情的那个我,现在连"明天跟朋友去外面喝酒"这样的决定都要在脑内预演父母的反应。原来成年不是一道毕业就能跨过的门槛,而是需要反复自证的过程。
某个深夜,当我第7次输掉游戏时,屏幕上的"失败"突然显得格外刺眼。
3. 我们这代人的温和逃避
凌晨三点的CS2界面亮着暗光,我突然意识到大学四年可能是社会给我们的最后一个缓冲带。在那里,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"我在找自己",可以把熬夜打游戏包装成"探索数字人文",甚至能把临时抱佛脚美化成"极限学习法"。
但毕业就像个突然被拔掉的充电头,所有自我欺骗的滤镜都失效了。我时常盯着书桌前的窗户发呆——玻璃上倒映着我和笔记本电脑的剪影,看起来像个标准的"有为青年"。书桌上的多肉植物正在枯萎,而我甚至没注意到它最后一次浇水是什么时候。
也许读研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拖延。就像把闹钟再往后调五分钟,我们这代人最擅长的,就是把重大人生的选择都变成温和的"再等等"。只是不知道,当所有缓冲地带都用完时,我们最终要降落在哪里。
但是我不想再逃避了。
- 1
-
分享